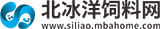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郑秋明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朱婧
小暑将至,西湖边,盛夏的荷风吹送。7月1日下午,来自南京的80后作家朱婧做客钱报读书会,在宝石山纯真年代书吧,与70后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黄咏梅对谈,围绕新书《猫选中的人》与读者展开讨论,聊聊关于文学,关于女性主义,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被看见”的她,男性凝视的视角、亲密关系、女性困境,以及每一种值得为她书写和讲述的爱。
朱婧,1982年生,小说家,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哥廷根大学“文化接触——作家驻留”项目作家,曾获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著有小说集《譬若檐滴》等。目前生活在南京,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同时她还是一位10岁孩子的妈妈。
大热天来到杭州的朱婧,长发披肩,娇娇柔柔的,有一些疲惫。面对读者,她坦言这个下午她有点犯困。像很多孩子还小的母亲那样,朱婧的日程表是缺觉的。要在日常生活中平衡好工作、育儿、写作的关系,她时常得对抗忽然而来的疲惫感。
2008年以后,她进入婚姻生活,读博、工作、生育,身份的嬗变,使她将近停笔10年,直到2019年出版了复出后的第一部作品《譬若檐滴》,重返文学现场。202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朱婧作品集《猫选中的人》,她的《猫选中的人》与当下新锐女作家张怡微、项静、周婉京、祁媛等人的作品一起,是名为“芳华说”的系列作品中的一部。
她不仅是一名生活者,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
《猫选中的人》是朱婧近三年的11篇短篇小说新作,呈现了她对这个时代中女性处境的观察。小说中,朱婧创造了一个有亲缘性的女性族群,她们大多性格温和,工作体面,是日常生活中没有攻击性的“好女孩”。她们的命运轨迹是可以被预判的,在人生长旅中,她们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孩子的母亲,或者丈夫的妻子,在家庭的消磨中,逐渐隐失,成为“不被看见”的女性。
生活中的朱婧。
从20岁出头在文坛崭露头角,朱婧成名较早。和之前的青春写作形成对比,她近几年的作品形成更加成熟、深刻、独特的主题和叙事风格,朱婧的小说是写给她同时代的人的。
这一场钱报读书会,引起了很多在场读者的共鸣。家庭日常婚姻中,女性要如何建立主体性,不成为“消失的她”?作者为“她”而写,“她”是谁?读书会的互动环节,有位女性读者提到女性更容易自我怀疑,丧失。
有读者问这本书为什么叫《猫选中的人》,朱婧回答时提到了女性的爱的启发,和婚姻中爱的救赎:“《猫选中的人》是其中一篇小说,也是书名。写作起点是和女儿在小区喂养了一只流浪猫,叫她“小渣”,取“琐屑”之意,爱怜它作为一个生命无可选择的微不足道,也因此观察到猫咪当妈妈喂养孩子的过程,是在观察猫的“母职”时,构想了这个小说。小说中男主人公自小与母亲分离,情感淡漠,后又遇母亲早逝。母子的疏离让他对亲密关系缺乏想象甚至逃避,是在和妻子的婚姻中,也是在对野猫的喂养中他获得爱的启发。母猫孕育出幼崽,帮助他与记忆达成和解,也认识到对母亲的愧疚和眷恋。理解爱,去建立人与人珍贵的联系,需要幸运与勇力,猫选中的人,是浓缩生命中奇迹性的时刻,所以要感谢猫。”
为母亲,为自我,为无数“她”发声,朱婧回应:“这一系列的小说,写的是本身不具有文学性的普通女性,她们也正是我熟悉和关心的人。小说在日常生活中聚焦女性经验的各种隐微处,也是一个让“不被看见的妻子”和“消失的母亲”的重现过程。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讲述,在书写,成为彼此的支持者,写作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存在,也由此联系过去而创造未来,这是女性写作的意义所在。为“她”而写,“她”是谁?是无数的女儿、姐妹、妻子和母亲,是她们,也是我自己。”
【为什么要呈现男性凝视下的女性】
钱报读书会:女作家的创作状态,你是非常真实的。期间写作中断十年,是空白可能又不是空白,你生活了,体验了。2019年以后的一系列小说,可以看见更为集中的目标方向,不是散点状。这几天有个电影《消失的她》,有评论也提到你小说里的“消失的她”,如第一篇《危险的妻子》,第二篇《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光进来的地方》等等,是一个写作者主动站在一个男性视角下写了这些女性,集中写了一类人物,就是妻子,甚至有些妻子名字都没有,也不怎么可爱,甚至有点笨,或有点弱。这个“男性凝视”,可能会让读者有一些不舒服,好像是一种俯视视角。80后女作家在我们印象中比较先锋,外向型的,面对世界更有力量,没想到你的小说场域是往回缩的,把一个女性主场完全缩回到家庭幽闭的内部。为什么这样处理丈夫眼中的妻子,你用了男凝视角,让作者躲在“我”后面审视女性,作为一个女作家为什么这样来写?
朱婧:这十年是具体的日夜,我也在家庭中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女儿成为妻子和母亲。在家庭中养成自我,在外部世界中确认自我,在文学所创造的世界中回望这个过程,家庭和女性成为我持续关注的对象。母亲家庭主妇的身份、传统型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我,让我理解到这种微渺对于一些女性来说也是全部;她们的哀乐,幸与不幸常常仅仅关系这微小空间中的私人事件。在这里我想写出真正的女性的经验,家庭生活中复杂的情感缠绕,为那些身处其中却无声的女性记录和发声。
女性因为长期的被凝视而被迫习得的,对于身体和感官过于苛刻的关注,会影响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形象,比如苗条体形作为女性美的文化理想,可以理解为是对具有异性吸引力的女性体形的追求,还关系传统定义中的“女性气质”,这些标准是如何被建立的?如何理解美、健康和食物的欲望之间的关系?文艺作品在其中如何发生作用?文艺创作中指向男性凝视的本质,是确保女性主体的描绘符合男性的品位和欲望。凝视不但关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也关乎自己看自己,将女性的日常变成艺术题材也可以视作一种为女性赋权的方式,女性写作可以留下女性世界的信息和自我定义的讯息,在我的小说中特殊之处在于多选用“他”视角。
一般来讲,女性作者如果选择“他”视角,很多时候是为了安全,避免他人在小说叙事者和作者之间产生联想。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女性作者而言,在用“他”时比起用“她”能够更好地建立一种性别对话。这样的写作和切入,确实会使得女性作家考量到男性的心理和目光。以这样一种心理建构来进入到由女性来书写的世界,你必须强迫自己利用另外一种性别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事情,比如呈现某种习焉不察的冷漠。同时会有一些暗示隐藏在这种性别对话里,比如我在使用男性视角时,想表达希望男性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会采取某种方式。
钱报读书会:《影》这篇小说,有个妹妹形象,阅读时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甚至想到了谋杀之类可能性,关于妹妹形象,为什么你想到写这样一个伪装,坏,复杂的女性形象,想给读者一个什么呈现?
朱婧:小说想说,当一个女性呈现出男性凝视的理想形象时,她是完美的,却未必是真实的,甚至是危险的,启发来自于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她描写来一个“清空男人的口袋,迎合男性的幻想”的女性,指出女性“是一个心里存在着一个观看女人的男人的女人”的本质。《影》中的妹妹,从小叛逆且具野心,长大后她知道男性幻想的是某种女性形象,而权利和资源属于男性,她就去扮演符合男性期待的完美女性,一旦用她的方法和能力控制男性的时候,她能够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她通过掌控男性来掌控生活,很是吊诡。
钱报读书会:《影》中的妹妹少女时代是反叛的,成年后的她是你前面小说中男凝下白幼瘦类型女性的一次反叛,在读了一系列克制的,看了令人压抑的小说之后,这个妹妹,她成了一个爆点。
朱婧在钱报读书会上。
【绝望的主妇和“消失的她”】
钱报读书会:最近因为电影《消失的她》,女性情感话题再上热搜,你小说中的第一篇《危险的妻子》,读了感觉也很像悬疑小说,略有惊悚感,书名也意味深长,平静当中潜伏着一种危机,不动声色。你这个小说写得特别讲究,似乎只展现了一个层面,明面上是闺蜜的那对夫妻的情感危机,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一个复调的互为镜像的结构。文中妻子的状态,也是一个危险的妻子,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硝烟味的战场一样,似乎很平静的相识,结婚怀孕生子,很平凡的过程,家庭生活的场景,你看到“墙上的斑点”,你引用了伍尔夫的小说隐喻,你当时的构思,是不是两组夫妻亲密关系都是危险性的关系?
朱婧:我的女儿玩公主系列的乐高,一定会把公主和王子放在一起。在整个被教养的过程中,会觉得那公主跟王子结婚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但是长大后会知道这不是终点,这可能是起点,甚至是驿站。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对家有一种想象,跟长久的被教养的方式有关,当然有很多人也不是这样,但是其实在很长时间我是确实有这样一份信仰存在的。
《危险的妻子》是我十年主妇生活的一个缩影,有大量日常内容在里面。小说中两个妻子,一个已经陷入和出轨丈夫的厮缠和争斗,另一个看起来体面完美,专心照顾家庭,和丈夫相安无事,但彼此有个默契:一旦丈夫离开家庭,他的外部生活妻子是不关心不追问的,保持一种不看不听的逃避状态。他们是大学相识结婚,是一起长大的人,但随着时间万事万物变化,新婚的房屋会变旧,墙上会生出霉斑,女性的可爱美丽会消失,假定的安全真的存在么?究竟谁是危险的妻子?家是不断在变化的,尤其它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你想让你的小家在变动的时代保持一种与世隔绝的安宁,是很难的。我也在《那般良夜》里讲父母辈的家庭生活。我想说那些看起来特别平安、特别传统的家庭里一样有动荡和不安,但是过去女性的发声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很多东西你可能听不到看不到,但是你回望时是能够感受到的。对我来说,家庭内部也是时代观察的前沿。家庭是女性情感、创造甚至智慧的凝结之物,守护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试图守住稳定结构中的位置,日常的失序和偏差难以避免,隐在的焦虑自然无处不在。
钱报读书会:你的小说刻画了一批绝望主妇,我想起村上春树写的购物狂太太,韩国电影里的全职主妇,也是中产家庭,妻子整天整理家务,烧各种美食,后来精神崩溃,把家里的小狗烹饪了,端给丈夫吃,感觉很惊悚。你用力刻画了这样一个群体,书写80后新女性的困境,是为80后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发言吗?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娃,是不是大环境促使你想要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朱婧:所谓新女性、旧女性,一旦进入某些角色,有些生活内容会变得相似,这也是我认为女性更能互相理解也更需要彼此的支持的理由。因从小受父母的爱护长大,获得充分的情感教育,知识训练和文学引领,爱和知识的给养,让我看起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我生育之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帮我照顾女儿,那是我跟母亲相处最为亲密的一段时间,我非常需要她的帮助,我的生活变成单调的喂养、哄睡、陪伴,活动范围窄小,几乎不太有社会交往。这时候不管我如何新,都和全职主妇身份的母亲生活在一种非常相似的状态里。孩子入托后,我恢复工作,2019年去东京访学,有一次在美术馆看画展,看到画作里的老式缝纫机。我想起母亲,想起小时候在她身边看她踩缝纫机,想起和她一起亲密无间的育儿时光,我意识到母亲这一生都不会有机会走出家庭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但是我走到这里,是经由了母亲的爱。我可以在中断十年重新工作,但母亲不能,这是我的感情的靶点,想要为她写些什么。
现场的女读者与朱婧交流。
【女性更勇于坚持建设亲密关系】
钱报读书会:你在《先生,先生》中,难得地写了一位关系中的女性强者形象。
朱婧:《先生,先生》原型是台湾学者林文月。2019年1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读中文系的人》,文题取自林文月先生同名散文,回顾自少年起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到后来成为中文系教师的经历,2019年4月我写成论文探讨林文月先生个人写作史的衍变,继又起意以林文月先生的经历写作小说。2020年1月,短篇小说《先生,先生》发表于《花城》杂志,以“宁先生”致敬林先生,写中文系的薪火相传。
在小说里,我也想讨论另一些问题。 “宁先生”生如满月,无论学业、事业、家庭都很圆满,但珍爱之人先她而去之后,她独处的漫长岁月并非总是朗朗乾坤、友伴围拥,而是有独处、有夜晚、有病痛、有衰老。我们如何去领受和理解死亡带来的果断和残酷的剥离,如何去存身。。
钱报读书会:其他的篇章包括《光进来的地方》等等,读来一个整体的印象是,这些妻子、女性感觉都有点不太聪明,是“白幼瘦”,小说里面写到这个男的喜欢的一个女孩,喜欢在茶水间贪小便宜,把公司的速溶咖啡都带回去,丈夫就选了这样一个女性成了她的太太。感觉这一系列作品里面的女性都处于强弱关系里的弱的一方,现实中80后女性很多也很强,但你关注的重点是一批弱势女性,你想要为她们发声的,因为她们是不被看见的,是有这样一个整体思考吗?
朱婧: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强与弱,我看到女性其实更勇于建设亲密关系,在生活的暗流和低谷里,女性常常能更保持坚韧和真实;母性身份带来的忍耐、奉献、利他主义的善良仁慈,这些都呈现出女性的力量。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女性,抑制自我近乎本能,保持着克制和体面是从少女时期就潜移默化地传达给我们的教养。有时女性看上去会在一些微小的点上爆发,因为没有容许女性随意释放情绪的空间和文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女性能够保证稳定的内核,保有真实的自我,平安地过完一生,都是强大的。
钱报读书会:作为内部环境或者说小环境中的女性,她们有很多无处安放的东西,包括《鼠妇》里的太太,我看到她的智慧已经无处安放了,所以做“低价猎手”展现了她的才华,作为一个出口。但她并没有能到一个广阔的地方去。读着读着,你需要长舒一口气。还有母亲的形象,《那天来临之前》里面的母亲,这个母亲跟父亲离婚,父亲先结婚,五年后母亲也结婚了,但作者的评判似乎有点复杂,我很欣赏这位母亲,恰恰她把握了她自己的生活,并不像现在的很多女性,在一个很烂的家庭环境里面沉沦。
你的小说中,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是疏离的,如《细路秘径》里的水清、冰清,母亲不希望女儿重复自己,小说中流动着幽微的母女之间的东西。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中,下一代会不会重复上一代伤痕的创伤的东西,怎么去规避?似乎《细路秘径》就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处理男女关系之外的亲密关系,是否已充分表达了自己想说的?
朱婧: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做了父母就不可以有自己,是不是做了父母就不可以犯错?反过来,儿女能否当父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生命有限的人?尊重他(她)的喜好、愿望、既有历史,接受他(她)的能与不能。《在那天来临以前》里,母亲坚持婚姻中应当有匹配的爱情,当父亲背弃母亲,母亲没有挽留父亲去保留婚姻的空壳,即使艰难重组,面对流言,也要重新开始。女儿想走正确的路给母亲看,发现自己也走不通,才能理解母亲。母女之间不仅应该有责任,也应该有彼此的爱,非常宽泛的爱,不仅是亲子之间的爱,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爱惜、怜惜。
钱报读书会:作品中独特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当代小说中,呈现的师生关系并不多,包括《先生,先生》、《细路秘径》、东京部分,可能在每个人童年成年之前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师生关系,联想到当下一些热点话题,师生关系里面男女高低位置不一样,你想重点讨论权力关系,还是类似古典语境里面的师徒式的美好关系,还是一种思辨的讨论?
朱婧:书中写了几类师生关系,其一,是中文系文心的承继。这关乎我的职业理想,关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二,想探讨隐秘的结构性问题。《细路秘径》,年轻女性对男性老师的景仰背后的社会现实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的可能。师生关系里,有社会性权利落差,就会存在种种陷阱。作为尊者师者的形象,他也是一个人,术业与德行,公德和私德德是不是一致的?但人们常常把它们并置,身在其中,保持清晰的判断非常难,这也是一种现实。
黄咏梅(左)。
【黄咏梅:朱婧式熟女写作】
70后作家黄咏梅在读书会上分享了自己读朱婧小说的感受,朱婧从青春写作转到熟女写作,有鲜明的个人写作特点和表达路径。她的小说场域从青春故事回到家庭,思考亲密关系中个体的孤独感。这是她十年沉淀的思考:“家庭生活中太太的角色,她肯定有很多想说的话。大多数篇章采取男性视角来看待妻子、女儿、母亲,这在女性作家里并不常见的,呈现了朱婧的勇气和能量。” 虽然小说写的场域都是家庭内部,但所涉及的问题可以放在整个社会来讨论,这本书敏锐地呈现了当下80、90后一代人的生存状态。
黄咏梅分享了对书名的理解:“整本书的题目《猫选中的人》。猫哪有理性?猫不可能选人,猫生是最宿命的。养过猫的人都知道,猫只是出于本能、习惯跟主人互动亲密。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跟猫的关系来说,他们就变成了一种被动,被选中、被需要。我觉得她小说里的人几乎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仿佛有什么东西主动为他们选择了生活,甚至意外和丧失的降临,都是被动接受的。朱婧就是写出了人的被动、服膺之下的自我的挣扎,写出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错位,我读到了那些被动状态背面的一种强有力的自主性。
黄咏梅关注到书中“危险妻子”,写出当下女性群体的精神困境:“里面写到好几个妻子其实都很危险的,不是指遇到具体的事情,而是女性在婚姻里面的精神状态。朱婧好像慢慢地安静地,在沙发上细心整理衣服一样去整理这些女性的精神皱褶。比如《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的太太,贤良乖觉,家务整理得很丝滑,遵守着日常伦理规则,看起来过得很优渥、自得,但就养成了一种被丈夫称之为“怪癖”的行为:白天,丈夫不在家 ,她会同时打开几台电脑,为了在网上各种打折区拼手速抢购,她的地下储藏室里屯满了廉价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她家是不可能用的,她讲它们送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这个举动背后是什么?一是无聊,在抢购得手时获得一些成就感,还有就是,把东西免费送给他人,她会获得一种奉献感以及被人需要的自我价值体现。小说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细微书写,呈现了当下一群女性的精神危机。小说里面,女主人公时常会在深夜路过厨房落地玻璃看到自己,忽然觉得很陌生,感叹:这个人难道就是我?”她们的自我会在许许多多个瞬间被看见。
黄咏梅指出,读者看起来,小说里的那些女性似乎在家务上是强手,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好像使人总体都感觉很弱。其实这正是朱婧的一种叙事策略,通过男性视角旁观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之弱,恰恰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去了解身边的女性,这是这本小说的核心所在。小说写出了亲密关系中个体的孤独感,也写出了女性不被男性所看见的那些部分。另外,小说中有几组母女关系,虽然代际间有错位,女儿不希望活成母亲那个样子,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活成自己的样子,比如《细路秘径》的水清和冰清的关系里其实是有一种和解和共识。”
黄咏梅盛赞朱婧的文字和“读中文系的人”的风格美感:“80后作家中,在我目力所及内,朱婧的小说辨识度挺高的。她利用“男凝”之下的女性,反观男性自身的局限甚至不堪,同时也展现出了女性在男性目光之外的生机和力量,这种叙事策略是很有意义的。她的小说里没有爆发点,但遍布危险,克制是她的力量所在。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作家,朱婧的文字讲究精准,尤其会出现一些读者久违了的字词,在读的时候,会停下来对这些字词斟酌一下,随后便会心她为什么会在此处选择用这样的字词,她的小说闪耀着汉语的丰富和光彩。
“转载请注明出处”